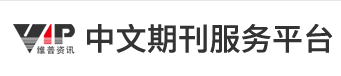伤寒研读
《伤寒论》六经若干问题(二)
姜春华
【摘要】
【关键字】
中图分类号:文献标识码:文章编号:
《伤寒论》六经若干问题(二)
四、 传经问题
《伤寒论》关于传经的几条条文,有似一日一经的,有的二三日、六七日、十余日尚在一经的,兹据本论及各家对传经的见解而讨论之。
《伤寒论》:“伤寒一日,太阳受之,脉若静者为不传,颇欲吐,若躁烦,脉数急者,为传也。”
这一条说伤寒一日是太阳受邪,脉静则病不发展,若脉数急而有欲吐烦躁等证,则病情发展。钱璜说:“伤寒一日太阳受之者,即《内经·热论》所谓一日巨阳受之,二日阳明受之之义也。”本论之六经与《热论》不同,钱氏之说非,然本条及下条又均似《热论》传经之说。
“伤寒二三日,阳明少阳证不见者,为不传也。”
《医宗金鉴》解释说:“伤寒二日阳明受之,三日少阳受之,此其常也。”按《热论》的次序是一日巨阳,二日阳明,三日少阳,与此条之次序颇相同,无怪后人以《热论》解释《伤寒》也。由上两条观之,似乎伤寒的常轨是一日传一经,不传则是“太阳邪轻热微”。后人因倘执定一日一经,将与后文矛盾,所以方有执另为解释说:“一日、二日、三日、四五六日者,犹言第一、第二、第三四五六之次序也,大要譬如计程。如此立个前程期式约模耳,非计日以限病之谓。”沈金鳌也认为:“一日约辞,非定指一日。”舒驰远说:“虽曰一日太阳,二、三日阳明、少阳,然不限定日期,必察其所见之证属于何经,若传至何经,又必转见何经之证,不然何所征验。”亦以为日期不限定,以见证为主。他们与方氏同,在见到某某证则曰入某某经,可见一日太阳二日阳明,以次相传之日数不必泥。
这两条的问题是: 首先提出了一日太阳,二、三日阳明、少阳的说法,与《热论》相同,而与本论另条矛盾。
“太阳病,头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,以行其经尽故也;若作再经者,针足阳明,使经不传则愈。”
成天己说:“伤寒一日至六日传三阳三阴经尽,至七日当愈。”其它如喻昌、钱璜、《金鉴》等,均用六日传六经为解;本条七日以上指的是太阳病,柯韵伯说:“夫仲景未尝有日传一经之说,亦未有传至三阴而头尚痛者,曰头痛是未离太阳可知,曰‘行’则与‘传’不同,曰其经是指本经而非他经矣,是七日乃太阳一经行尽之期。”由这一条七日尚在太阳,与上条一日一经之说是有矛盾的,或谓前条为假拟之辞,非实同《热论》之日传一经,但另条更明白。
尤在经注:“按《内经》云,伤寒一日,巨阳受之云云,又云七日太阳病衰,头痛少愈云云,盖伤寒之邪有离太阳而入阳明者,有遍传诸经而犹未离太阳者,此太阳病头痛至七日以上自愈,正与《内经》之旨相合。”按尤氏素称博洽,于此乃极不通,焉有邪既留太阳又遍传诸经,邪既遍传六经,何不见六经证耶,谓与《内经》之旨合,谬矣。
“伤寒三日,三阳为尽,三阴当受邪,其人反能食不呕,此为三阴不受邪也。”
此条说得很明白,前之三日为三阳,后之三日为三阴,与《热论》冥合无间,所以汪琥说:“伤寒三日者,即《素问》相传日数。”沈金鳌于前条解释一日、二日是“约辞”,在此条却说“三日三阳为尽,三阴当受邪,三阴必先太阴脾。”这里不再作“约辞”,而确定了三日传三经了,沈氏前后不照应,自相矛盾。
“伤寒三日,少阳脉小者,欲已也。”
此条仍是一日一经之意,与前说同。
由于《伤寒论》中对传经之文,有一日一经和六日一经,所以后人有执着一日一经的,有认为不拘日数的,也有调和二者之说,认为一日一传是“经气”,不拘日数是“病气”等等。兹分别讨论于下。
1. 可以循经传、可以越经传、可以自受、可以直中
戴元礼说:“伤寒先犯太阳,以次而传,此特言其概耳,然其中变证不一,有发于阳即少阴受之者……亦不循经而入,如初得病径犯阳明之类,不皆始于太阳也;亦有首尾止在一经,不传他经;亦有止传一二经而止者,不必尽传经也。至如病之逾越,不可泥于次序。”戴氏此说是从全论内容结合临床实际的体会。本论中有一日传,亦有七日未传(一日传一经有之,但非六日传尽六经之意)。有始终一经,有一二经即止者。有初病即犯阳明,直中阴经者;临床所见亦确如此,故戴氏不拘于日传一经,六日传遍之说,最为合理。王海藏亦认为能循经传,亦能越经传,王氏更分别顺逆传,上下传、误下传、表里传,又有传本、传里、循经得度等名,虽嫌支离,要之说明不必循序耳。
吴绶说:“阳邪以日数次第而传者,一二日太阳,二三日阳明,三四日少阳,四五日太阴,五六日少阴,六七日厥阴。”吴氏用《伤寒例》太阳病一二日发,阳明病二三日发之语,不肯定一日二日,而用约辞。又引《活人书》说:“寒邪首尾只在一经而不传者有之,有间传一二经者,有传过一经而不再传者,有足经冤热而传入手经者,有误服药而致传变者多矣。”又说:“热邪乘虚之经则传也,若经实则不受邪,而不传也。”吴氏说同戴氏,末言虚则传,实则不受,言简意赅,为不循序作了合理的解释。氏更从五行生克说,而有夫传妻,妻传夫,母传子,子传母等说,殊无意义。
近人章太炎说:“《伤寒论》‘太阳病六七日’,‘太阳病八九日’,‘太阳病,过经十余日’,又云‘阳明居中土也,无所复传’,又云‘少阳病得之一二日’,‘少阴厥阴得之二三日’,是伤寒非传遍六经,三阴病不必自三阳传致,更无一日一经之说也。叔和序例,引《素问》以皮傅,后人转相师法,遂谓一日太阳,二日阳明,三日少阳,四日太阴,五日少阴,六日厥阴,刘守真见世无其病,并仲景《伤寒论》而疑之。然如正阳阳明之非受传,少阴寒证之直入,虽《活人》与成无己亦不能有异言,则知《伤寒论》本与《素问》不同。”章氏说得很对,但他也同柯氏一样,说本论中无日传一经之说则非。我们如果从本论全文看,则传经的情况实如戴、章诸氏的见解,肯定本论不是用《热论》一日一经之说,本论之一日太阳,二、三日阳明、少阳不见为不传,及伤寒三日、三阳为尽、三阴当受邪等条,可能是王叔和掺入,因其既取《热论》作序例,自可能掺入与《热论》相同之资料;或者前人传抄混入,叔和不辨而取之;或者叔和之后,为求符合《热论》之说者所掺入,虽未可知,总之一日传一经之说,与本论全部精神不符。仲景著书,决不会自乱其例,自造矛盾。戴、吴诸氏以为有一日传一经,有几日在一经,盖见其矛盾而为之解,殊不知纵有一日在一经,然论中绝无一日传一经,六日而传尽之证据,况“三日三阳为尽,三阴当受邪”之语气,其指一日一经何等肯定,其违背全论之精神亦何等明白,又何必曲为之说耶!章氏为朴学家,其说虽原自戴氏,但言必有征,故以引经证经之法,引述论中诸条,证实有多日尚在一经,三阴不必自三阳传入,正阳阳明之非受传,少阴寒证之直中,试取全论而观之,何有于日传一经六日六经之证耶?
2. 六经以“气传”而非“病传”说的问题
因为《伤寒论》中传经之说有矛盾,后人不知系掺入的资料,乃设法为之圆说,首先提出气传病传者为张志聪氏,他说:“厥阴为一阴,少阴为二阴,太阴为三阴,少阳为一阳,阳明为二阳,太阳为三阳,故《素问·至真要大论》论六气司天,六气在泉,皆始于厥阴,终于太阴,无病之人,六气循行,亦从厥阴而少阴,少阴而太阴,太阴而少阳,少阳而阳明,阳明而太阳,若伤寒一日太阳受病,则从阳而阴,由三而一,须知本论中纪日者言正气也,传经者言病气也,正气之行每日相移,邪病之传一传便止。”
其言之似乎成理者为张令韶氏,陈修园亦受其迷惑,引入浅注中作读法。张氏说:“传经之法,一日太阳,二日阳明,六气以次相传,周而复始,一定不移,此‘气传’而非‘病传’也。本太阳病不解,或入于阳,或入于阴,不拘时日,无分次第,如传于阳明则见阳明证,传于少阳则见少阳证,传于三阴则见三阴证,如下文明言少阳证不见者为不传也,伤寒三日,三阳为尽,三阴当受邪,其人反能食不呕者,此为三阴不受邪也,此病邪之传也。须知正气之相传,自有定期,邪之相传,随其证而治之,而不必拘于日数,此传经之大关目也。不然,岂有一日太阳则先头痛发热等证,至六日厥阴不已,七日来复,又见头痛发热之证乎?此必无之理也。”张氏说的气传,好似人体正常生理,言人体一日气在厥阴,至第六日在太阳(他说正常时,气自里达表。)此气若指经中之经气,则是一日夜五十周于身,不是六日一周于身,看他所说的气,实是指本经应天之气,如太阳、即太阳寒气,阳明、即阳明燥气,他在前段文章中大谈天人说:“太阳之为病,兼气与经而言之,何谓气?则太阳之上寒气主之;何谓经?则太阳之脉连风府,上头项,挟背抵膝足,循身之背,足太阳膀胱之经脉”。他认为人身经脉上应天气,引《素问·天元纪大论》说:“寒、暑、燥、湿、风、火,天之阴阳也,三阴三阳上奉之。”又日:“厥阴之上,风气主之,少阴之上,热气主之,阳明之上,燥气主之,太阳之上,寒气主之。天有此六气,人亦有此六气,与天同体者也。”他以为天有此六气,人身也有此六气,因此他说:“天之寒气感于人,人即以己之寒气应之,所谓两寒相得,两气相从者也。”至于人体的寒气是什么呢?则以“足太阳膀胱为寒水之脏”而“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应,是太阳又主通体之毫毛,而为肤表之第一层。”又说:“三阴三阳上奉天之六气,下应地之五行,中合人之脏府,合而为一,分而为三。”张氏这些说法有好多问题:
(1) 张氏误解《内经》的三阴三阳上奉之。《内经》是讲的天地之气,不是讲人的三阴三阳。张氏误以为人的三阴三阳上奉天之六气。
(2) 天之六气是一年之气,逐节轮换,并非六天一转,人体之六经经气,也要逐节轮转方能符合六气,张氏前面说气传一日一经,六天一转,一个是一年一转,一个是六天一转,如何相应?
(3) 太阳膀胱可引经文“毫毛其应”牵到肤表,六气之邪多有表证,又以何理来说明毫毛为肤表之第一层。
(4) 如果说人体六经之气六日一轮回,则凡人伤寒,必在第六日太阳主气之日,余五日不同气即不感受,宁有是理?
(5) 如果所说的气是太阳的寒气,阳明的燥气,则应该每天每时都在本经上行,用不着传,如果一传,则今天的太阳之气到明天已非太阳,各经轮回相传,均非本经之气,谈不上本经之气了。
因为张氏提出了气传、病传的不同,魏子千就问:“伤寒六气相传,正传而非邪传固已,不知无病之人,正亦相传否?不然正自正传,邪自邪传,两不相涉;正传可以不论,何以伤寒必计日数也?”张氏答:“无病之人,由阴而阳,由一而三,始于厥阴,终于太阳,周而复始,运行不息,莫知其然,病则由阳而阴,由三而一,始于太阳,终于厥阴,一逆则病,逆道则甚,三逆而死矣。”张氏以气传从一而三,则《内经》少阳为一阳,阳明为二阳,太阳为三阳,自内而外之说,如此,则此六气之行,由内而外,一日在最内之厥阴,至第六日乃外达于太阳,当第一日唯厥阴有气,第六日亦唯太阳有气,此气六日之中惟一经有气,余则无气,无气尚是活经耶,据修园说:“无病之人,经气之传,无所凭验。”则此“气传”乃无凭之说也。又病则由三而一,由外而内,当亦必依经而行,不会错乱,不错乱故可计日。事实上病之发展并非如此,张氏亦自知其不通,故末了说:“吾友高士宗云,读论者因证而识正气之出入,因治而知经脉之循行,则取之有本,用之无穷,若执书合病以求治,则非矣。”这一段话无异推翻了前面每日逆行一经之说,其进退维谷如此。
蜀人郑钦安,可能亦受张氏影响,有一气分为六气图说,自外而内,画六圈,外则太阳寒气,内之最后则厥阴风气,他说:“今以一圈分六层,是将一元真气分为六气,六气即六经也。气机自下而上,自内而外,真气充满周身,布护一定不易,外邪入内,先犯外之第一层,第一层太阳寒水,气化出路,故畏风恶寒,治之不当,邪不即去,渐至第二层,二层乃阳明所主,阳明主燥,外邪至此,化为燥邪,故恶热,治之不当,邪不即去,渐至第三层,三层乃少阳所居,半表半里之间。……”郑氏不谈天人相感,亦不谈经气之传,似无纰漏,惟将一元真气化作六气,亦即六经,未免杜撰,且如所作图,层层而入,岂每病皆按次序循行乎,不如戴、吴诸说远矣。
结语
(1) 本论中有日传一经,亦有六七日、十余日尚在一经,其一日一经,不符全论精神,当为后人增入以求符合《热论》。
(2) 有人体会为约模定程,有认为可以循经传,可以越经传,亦可直中,较大符合临床实际。其日传一经,肯定不符事实。
(3) 六经“气传”而非“病传”之说,为避实逃虚法,理论不通。
(4) 一元真气化六气为六经,有违《内经》经脉。
五、 六经提纲问题
《伤寒论》原无提纲二字,后人称每篇之首条“某某之为病”为提纲,说这一条为全篇的纲领,是本篇的主要证,大家都很重视。柯韵伯说:“仲景六经各有提纲一条,犹大将立旗鼓,使人知有所向,故必按本经至当之脉证而标之。”其实每篇的第一条(阳明篇在第二条)不能作为本经证候的提要,即不能作为提纲,可能是王叔和或后人拟入,或就原条文拟改,决非仲景所作。因为提纲是足经的证状,而这些证状不能代表本经篇内的证状。例如:“太阳之为病,脉浮,头项强痛而恶寒。”方、喻诸家,以为“此为太阳之总冒,以下凡一提及太阳病,即具此证、此脉”。果如所说,则第二条“太阳病,及热,汗出恶风,脉缓者,名为中风”。第三条“太阳病或已发热,或未发热,必恶寒体痛呕逆,脉阴阳俱紧者名为伤寒”。一则恶风,一则恶寒,一则脉缓,一则脉紧,各不相同。且第六条“太阳病发热而渴,不恶寒者为温病”。此则明言不恶寒,与第一条之恶寒相反,如何可以说凡太阳病均具此脉证呢?柯氏以为“脉反沉,头不痛,项不强,不恶寒,是太阳之变局”。然则唯提纲始算正证,它皆变证,正证何少,变证何多耶?既是变证,仍冠以太阳病何也?曲为提纲作护,强词夺理。
阳明病第一条有太阳阳明、正阳阳明、少阳阳明的问答,第二条始曰“阳明之为病,胃家实也”。与各经篇首条例不同。少阳篇第一条曰:“少阳之为病,口苦咽干目眩也。”按189条阳明中风亦有口苦咽干之证,而此乃专作少阳提纲,可怪。按例言,提纲为一篇之主证,其中不应谈及具体治疗,乃太阴篇“太阴之为病,腹满而吐,食不下,自利益甚,时复自痛,若下之,必胸下结鞕”。厥阴篇提纲亦有“下之利不止”语,不复成为提纲。少阴病之亡阳厥逆,实为要证,而提纲中一字不提。厥阴病只提消渴,气上撞心,心中疼热,饥而不欲食以及吐蚘等,与本篇中所言不相关,而本篇中之厥多寒少,厥少寒多,先厥后热,先热后厥,以及下利厥冷等要证反不一提,不成其为提纲(厥阴55条,其中下利二十八见,厥冷廿见,厥热交错十见,渴欲饮水吐蚘仅一见,且此二条渴非消渴,吐蚘乃蚘厥)。后人不怀疑提纲之非仲景所作,反尊之为一篇之纲领,曲为之说,柯氏更生出“提纲是正面,又要看出底板,细玩其四旁,参透其隐曲。”似乎仲景要故意使人难解,作出谜底,使人猜谜似的。看提纲那里有什么正面文字。柯韵伯自己知道提纲与内容不同,乃又说不仅为伤寒而立,是赅杂病而言。吴坤安亦说:“六经主病,仲景非专为伤寒立言,如厥阴所述,气冲吐蚘等证乃厥阴风木自病,不拘伤寒杂证,但见呕逆吐蚘者即是肝邪犯胃,宜兼厥阴而治。”远些都是知其不可通而求其通的理论。
我的看法,欲识本经之证,只有从本经中全面来看,除误治转变之证外,总汇其证,此若干证即该经之病。虽证不必悉具,但应有其主要的若干证,提纲可有可无。原来提纲既无本经主证,则临床参考价值可疑,而且自从有了提纲,反使一般人印定了“伤寒是足经病”的观念。
结语
(1) 六经提纲非仲景所拟定,为后人拟入。
(2) 六经提纲不符各经主要证候,实用价值不大。
六、 六经次第问题
《素问·热论》一日巨阳、二日阳明、三日少阳、四日太阴、五日少阴、六日厥阴。今本《伤寒论》编排六经之次第与之相同。若依病情发展论,则《热论》之次序,正说明由浅及深。惟《伤寒论》之病情,太阳为初起,阳明有初病即成,少阴即曰得之一二日,则亦病之初起;太阴、厥阴,亦不必来自太阳;既非由浅及深,则其次第不必与《热论》同。后世有议之者,如戴元礼、丹坡元坚等。戴氏说:“太阳在表,少阳在表里之间,阳明在里;自外渐入内,次第正当如此;果如《伤寒论》中所说,一日太阳,二日阳明,三日少阳,岂可第二日在里,而第三日方半表半里乎?”丹波著《述义》,其次第一为太阳,二为少阳,并说少阳为半表半里之症,仲景即拈之于太阳篇,唯其名则取之《内经》,是以更摘其概列,之阳明之后,今先立于阳明者,使人知传变之叙而已。(节要)
张子和《伤寒心镜》说:“庞安常谓: ‘阳主生,故足太阳水传足阳明土,土传足少阳木,为微邪。阴主杀,故木传足太阴土,木传足少阴水,水传足厥阴木,为贼邪。’盖牵强附会。”他不承认这个次序的合理,另引《素问·阴阳离合论》之言以证《伤寒论》之篇次,他说:“太阳根起于至阴,名阴中之阳;阳明根起于厉兑,名曰阴中之阳;少阳根起于窍阴,名曰阴中之少阳;太阴根起于隐白,名曰阴中之阴;少阴根起于涌泉,名阴中之少阴;厥阴根起于大敦,名曰阴之绝阴,其次序正与此合。”意谓《内经》太阳之次为阳明,阳明之次为少阳,而与《伤寒论》之次第相同。但这也只证明六经的次序与之相合,并没有说出什么理由。
《伤寒论》原来概论伤寒杂病,后人将它分开。虽条文有某某病之称,当时并未分篇,应无次第可言。王肯堂说:“王叔和编次张仲景《伤寒论》立三阳三阴篇,其立三阳篇之例,凡仲景曰太阳病者入太阳篇,曰阳明病者入阳明篇,曰少阳病者入少阳篇;其三阴篇亦依三阳之例,各如太阴、少阴、厥阴之名入其篇也。”这个推测是很有理的,因为从六篇的内容来看,除有六经标目的条目外,其它归类有很多不惬当的,要是仲景自己分篇,决不如此。王氏说:“其或仲景不标三阳三阴之名,但曰伤寒某病用某方主之而难分其篇者,则病属阳证发热结胸痞气蓄血衂血之类皆混入太阳篇,病属阴证厥逆下利呕吐之类皆混入厥阴篇也。惟燥屎及屎硬不大便大便难等证,虽不称名,独入阳明篇者,由此证类属阳明胃实,非太阳厥阴可入,故独入阳明也。所以然者,由太阳为三阳之首,凡阳明、少阳之病皆自太阳传来,故诸阳证不称名者皆入其篇;厥阴为三阴之属,凡太阴、少阴之病皆至厥阴传极,故诸阴证不称名者皆入其篇。”王氏将这些问题指出,对于理解六经的面目是有意义的。清代高学山氏肯定原书不分篇,所持的理由是可信的,他说:“仲景《伤寒论》原书必不从六经分篇,当只是零金碎玉,挨次论去耳,分从六经者,其王叔和之臆见。盖病虽不能逃六经,而六经亦何能限病哉,既从六经分篇,则一病而界于两经之间,及一条而有二三经之变证者,将何所收受乎?且不必逐条冠之曰太阳病、阳明病等之字样矣。”仲景书每条之上冠以某某病,正说明其原始不分篇。高氏之见极是,后世争论少阳与阳明之先后次第者可谓多事矣。又王肯堂以为六经条文分篇不惬,尚未知《伤寒论》中混有杂病条文,而杂病篇中亦混有伤寒条文,不但六经分篇之不惬也。举例言之,痉湿暍诸条之太阳病,中风历节篇之少阴脉浮而弱,水气篇之太阳病,黄疸篇中阳明病脉迟、食难用饱云云。他如无标目消渴篇之脉浮发热渴欲饮水小便不利猪苓汤,渴欲饮水口干燥者,亦伤寒之条文。
结语
(1) 六经原始当不分篇。
(2) 叔和将阳性证混入太阳,阴性证混入厥阴,遂乱其例。
七、 六经统百病与为伤寒而立的问题
本论六经,有人认为为百病而立,不仅伤寒。也有认为是为伤寒而立。按本论以三阴三阳统概表里寒热虚实,任何疾病,其诊治之理,当不出其范围。张志聪说:“本论虽论伤寒,而经脉脏府阴阳交会之理,凡病皆然。”的确,以此高度概括性的阴阳以审察疾病属性,分析病情进退,推测病理过程,掌握治疗之攻补,实为临床之关键,固属凡病皆然,不仅伤寒为然也。
据本论自序“为《伤寒杂病论》合十六卷”既称伤寒又曰杂病,更申之曰合十六卷,则原书系伤寒杂病并论可知矣。但虽系并论,其中仍有分别,其称“合为十六卷”可见二者之分合,推其原来叙述,凡伤寒之类的热病,如六气之病,当概在伤寒之内,其伤寒中有特殊型者,则入于杂病,其杂病之有共同型者,则又入于伤寒,其中分而不分,不分而分。叔和将伤寒与杂病划而为二书,致后人误以为六经是为伤寒一病而设,与它病无关。柯韵伯知其失,特矫枉过正,遂谓六经可概杂病。柯氏说:“原夫仲景之六经为百病立法,不专为伤寒一科,伤寒杂病,治无二理,咸归六经之节制。”说治同一理是对的,说咸归六经之节制则非。当然,人身全部不出十二经脉范围,可是仲景六经之证显然不能概括杂病篇之证。柯氏说:“夫仲景之六经是分区地面,所该者广,虽以经脉为经络,而不专主经络上立说,凡风、寒、湿、热、内伤、外感,自表及里,有寒有热,或虚或实,无乎不包。”其言仲景六经名为经而实非经是对的,说六经表里寒热虚实也是对的,但说内伤、外感无不包,就有问题,因为柯氏混淆了伤寒与杂病二者的共同性和特异性问题。柯氏又说:“如太阳之头项强痛,阳明之胃实,少阳之口苦咽干目眩,太阴之腹满吐利,少阴之欲寐,厥阴之消渴气上撞心等症,是六经之为病,不是六经之伤寒,乃六经分司诸病之总纲。”柯氏此言非常牵强,因其不知提纲为后人拟增,遂不顾提纲之纯为足经证不概手经,且此六经提纲又不能概括六经之主要证,何可言是六级之为病而可以作为分司诸病之总纲耶?柯氏又说:“观仲景独于太阳篇别其名曰伤寒、曰中风、曰中暑、曰温病、曰湿痹,而他经不复分者,则一隅之举,可以寻其一贯之理也。”柯氏不知六经本不分篇,又不知中风、中暑、湿病,其初期皆有大同之共同证,故皆可称太阳病,因其初起又有异,即因其异而有中风、中暑、伤寒之别;又因其病本不同,发展殊途,故六经之中,又各有中风之名。柯氏又说:“其他结胸、脏结、阳结、阴结、瘀热发黄、热入血室、谵语如狂等证,或因伤寒或非伤寒,纷纭杂沓之中,正可以思伤寒杂病合论之旨矣。
盖伤寒之外皆杂病,病名多端,不可以数计,故立六经而分司之。伤寒之中最多杂病,内外夹杂,虚实互呈,故将伤寒杂病合而参之,正以合中见泾渭之清浊,此扼要法也。”柯氏说结胸、脏结、瘀热发黄等,或因伤寒或非伤寒,这是对的,说伤寒中多杂病,也是对的;因为结胸可由杂病误下而成,发黄亦见于杂病,而伤寒过程中因患者某些脏器之素虚,病邪因其虚而传入,则见杂病之证。惟杂病终不得与伤寒混淆,因杂病伤寒均各有必见之“正证”,不得因其变证而混淆病之“正证”。柯氏说:“杂病之名多端,不可以数计,故立六经而分司之。”夫此区区六经之提纲,能司不可以数计之病耶?柯氏苟平心思之,当知其不可通也。
古代伤寒与杂病之分,吾人似不能用现代的疾病分类而讨论之,如以为伤寒为急性传染病,杂病为内科各系之疾病,则不惬当。因《金匮》之疟疾、痉病、黄疸,皆现代之急性传染病,《伤寒论》中之太阴病,则《金匮》腹满宿食之类,如用现代分类,则痉病应属伤寒,太阴病应归杂病。但从总的来说,则中风、历节、疟疾、百合、狐惑、阴阳毒、消渴、水气、虚劳、肺痿、肺痈等,皆为独立之疾病,有特殊的自成一系的证状,而伤寒则为较广泛的,有共同性的一系的证状,仲景当时可能以普遍共同性的作为伤寒,以各个特殊性的作为杂病,伤寒以证分类,故重在辨证论治;杂病以病(中医学概念之病)分类,故重在辨病施治。但二者是辨证的结合,治症之中有治病,治病之中亦辨证,二者非绝对的。举例言之,如黄疸篇之有谷疸、酒疸、女劳疸之别,方法有茵陈蒿汤、茵陈五苓,前者用大黄之苦寒,后者用二苓之淡渗,虽同以茵陈为主,其不同如此。更有栀子大黄、硝石矾石诸方之不同。又如“脉浮以汗解,桂枝黄耆汤”,“哕者小半夏汤”,“腹痛而呕小半夏”,“腹满小便不利大黄硝石汤”,“酒黄脉浮先吐,脉沉先下”。又如疟病篇,“脉弦小紧者下之,脉弦迟可温,脉紧可汗,脉大可吐”,“温疟身无寒但热,白虎桂枝汤”,“疟多寒,蜀漆散”,是皆治病而结合辨证也。蜀漆(常山苗)、柴胡为治疟病之有效药,而石膏、知母、桂枝、干姜则又治热以寒,治寒以热之辨证对治法也。黄疸之用茵陈、栀子、大黄,似为对病施治,然亦须辨证。至于桂枝加黄耆用于黄疸似乎治症,为解表而助正法,小建中汤(桂枝加饴糖)治黄而小便利,则调和营卫又补其中,其辨证施治之精神又如此。此类辨证施治之方法不能谓无治病作用。至于《伤寒论》中治法重在祛邪以安正,正虚则重在扶正以祛邪,处处主动,以解除人与病之主要矛盾问题,并非单纯的以解决证候为主,故辨证论治决非对证施治,其实质是以机动的方法解决人与病的主要矛盾为主的。
《伤寒论》六经虽不必统百病,但其中辨证论治的精神法则,却可应用于百病,而其中的方药更可广泛应用于各种疾病,并非伤寒方只治伤寒,也非古方不适用于今日,只在如何理解六经中之辨证精神,以及方剂组合的主要作用,则多病可用一方,一病也可用多方。举例言之,如118条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,原治火逆下之,因烧针烦躁者;112条医以火刦迫之,亡阳惊狂,亦用枝桂龙骨牡蛎等,再从药物之作用测之,则此方乃治正虚者,有温补收敛安神等作用,可活用于虚寒性之下利、久痢不止、痰饮之水走肠间、吞酸吐水、咳唾多痰、自汗盗汗、白带漏下、梦遗滑精、鼻涕过多、耳流脓水、痰核溃疡、心悸怔忡、夜卧不安、小儿多惊等。举一反三,他可类推,故吾谓六经统百病之说有问题,惟六经之方可施之于百病则无问题。
结语
(1) 《伤寒论》之理法方药可用于百病,其六经提纲则不能概百病。
(2) 伤寒与杂病原不分,因其不分,可以看出同中之异,异中之同,合中见泾渭之清浊。
(3) 伤寒以共同证为主,故重在辨证论治,杂病以特异证为主,故重在辨病施治,但二者并非绝对的,而是辩证的,治证亦达到治病,治病亦必须辨证。
总结
1 由于伤寒杂病本是混合,而六经也原不分篇,后人既将伤寒与杂病分为二书,又将六经分为六篇,以是混乱了原作的共同性中有特异,特异性中有共同,二者参互出入,提示同中有异,异中有同的精神,以及疾病开始与发展既有共同,又有不同的情况,而造成了一律阶段化。吾人欲理解伤寒杂病与六经实质,必须不为今本《伤寒》《金匮》编次所拘,从其全面而理解之。
2 《伤寒论》六经之名来自《内经》,但其内容实质已非经络之旧,作者融会《内经》全部阴阳概念,包括了表里寒热虚实经络脏府营卫气血邪正消长等,成为一个多种概念的高度综合体。它不是单纯的经络,也不是单纯的地区和病程划分,更不是简单的证候群。后人不从六经全部精神与《内经》的全部阴阳概念来联系体会,而拘拘于《伤寒》六经中某些符合于《内经》经络途径的证状为说,因此不能阐明仲景六经的实质。吾人欲认识仲景六经,必须从《内经》的全部阴阳概念(包括经络脏府气血营卫等)来理解,决不可单纯的用某些观点来理解,否则就会陷于片面。
3 传经问题的造成,一是由于前人将《素问·热论》加于伤寒之首,致后人将两种不同的六经证候和传变混为一谈,这是造成历史上纷争的一个主要原因;二是由于后人因《内经·热论》有日传一经,六日传遍六经之说,乃掺入类似日传一经之条文于《伤寒论》中,以求符合于《热论》,致造成《伤寒论》中传经日数的矛盾;三因《热论》六经是足六经证,后人为求得一致,乃掺入足六经证之提纲,遂致产生了伤寒传足不传手,伤足不伤手等谬论。吾人应删除《伤寒论》首的《热论》文字,不受《素问·热论》传经说影响,并从全论中理解传经的实际情况,摒除其日传一经不符全论精神的条文。
4 六经中有手经证,而六经提纲只是足六经证,且提纲又不能提示一经中主要证候,既不能起指导作用,反印定了人们传足不传手的观点。吾人欲理解六经证候,应从六经各篇条文中前后参考汇合,从而分别证候之主副,知某经应具某证,一见某证即知属于某经。
5 六经证状虽不能概括百病,但六经方剂尽可应用于百病。吾人应从六经的实质精神理解方剂的作用,从而以之应用于百病,不为伤寒一病所限,不为六经一证所拘,达到异病同治,同病异治的作用,并达到辨证论治与辨病施治辨证的结合。
姜春华论临证近代名老中医经验集